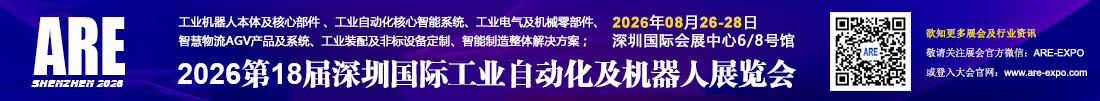统计市场上的少儿编程产品可以看出,虽说种类挺多,但是少有独具特色和品牌价值的产品。虽然各家都会宣传自家产品的优势,格物斯坦认为借鉴国外产品加上少部分自主研发的课程体系,客户很难从中辨别哪个产品更好。加之少儿编程培训作为新事物,它还没有形成权威、统一的评价体系,家长对它很难在短期内有很深的认同,因此它在跟学科辅导班、兴趣特长班抢夺孩子的业余时间上就会占上风。

虽然现在很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公司一年才几百万到千万级的收入,但不妨碍估值都是十亿美金起。所以,教育机器人领域创业是大坑还是大机会还真是说不好。前天跟某位搞机器人的朋友在办公室聊机器人怎么与教育结合。我们聊了三个小时,结论是 2C 服务领域的机器人基本还都是弱智加残废,想要它给你端杯水点个烟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了。
市面上那些只会翻跟头、做俯卧撑的小机器人都要几千块钱,孩子买回去基本上两天就玩腻歪,然后扔到角落吃土了。反正都是吃土为什么不买几百块的扫地机器人呢?人家专业吃土的啊!

不同从业经历的创业团队对企业的经营思路明显不同:技术出身的人,知道用哪些技术能够提升体验,但往往忽略教育的本质是理念和内容,而不是技术载体;教育背景的人,可以注意到儿童内心的变化,但有时过分强调理念、情怀和内容,忽略技术载体的作用;渠道出身的人能够迅速感知市场需求,但可能并不懂技术,也不很懂内容,简单的通过OEM做产品实现,很难有沉淀。
近年来,在政策加持和资本推动的双重作用下,国内外青少儿教育也掀起了学习编程的大潮。但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,少儿编程教育行业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。
疫情之下,少儿编程行业的线下布局遭受重创,特别是以机器人编程为主的一些线下少儿编程教育机构,损失可谓惨重。企业承担着高昂的房租与人工成本,但近期却无法开门营业,不开门就意味着没有收入。疫情对业务的影响可能不只是损失两三个月营业额那么简单,有些机构甚至会现金流断裂,面临倒逼的风险。即使熬过这次疫情,也可能会元气大伤。

综上所述,面对这样一个跨领域、多学科交叉的课题,团队内部融合各类人才,外部合作上与长于不同方向的企业达成合作、在提供的要素和获得的价值间取得平衡,成为必然的选择。